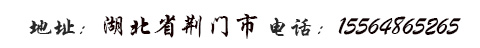罪孽的报应第十章两座普通小城6
|
北京治疗白癜风医院哪个好 https://m-mip.39.net/disease/yldt/bjzkbdfyy/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|卷四 历史学者尝言:“过去深入骨髓。”身为世人眼中的危险民族“,德国和日本如何应对自己不光彩的过去?他们是如何看待记忆战争的?又如何在历史的罪孽中审视自我?”没有危险的民族,只有危险的情境。”实际的政治安排,往往比所谓的历史规律和民族性格,更能影响一个国家在面对自身历史遗留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。 然而,就多数人的情况而言,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其实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。当直面令人不悦的事实时,日本人的反应和德国人差不多。多数人不是转身离开,就是捶胸顿足。年,大馆市举办了一场题为“花冈事件”的小型展览。我见到一份特地为此准备的问卷。参观者被要求写下自己的年龄,是如何得知“花冈事件”的,以及对此的感受。人们的回答和德国纪念馆留言簿上的话差不多——都在表达“民族”耻辱。“日本人是全世界最野蛮的民族!”一位年过三十的男人写道,“作为日本人,我感到深深的愧疚。”关于花冈事件,他是从父母那里听来的。另一名参观者是年逾花甲的老媪,事发当时便知情。她写道:“作为花冈人,作为日本人,我感到无地自容。这跟‘花冈事件’相比或许只能算是桩小事,但我希望人们知道,家父过去利用华工为他工作,自己却借用上司的名义,假装是他们下的命令。”公开悔过——或者用中国人的话来说,叫“自我批评”——并不只在基督教文化里才有。 谷地田打小就是基督徒,但他说自己“耻于”提及。他自视为一介凡人,一位社会主义者。基督徒在日本东北的小镇里并不鲜见传教士吸引的是穷人,这在哪儿都一样。谷地田的老婆孩子既不是基督徒,也对他有关华工的研究毫无兴趣。太太因为他常去中国怨言颇多,希望老公能带她去欧洲度假。女儿小时候曾帮爸爸分发工会传单,但年纪一大,就对他的事再也不闻不问。儿子则向来不感兴趣。跟我说起这些的时候,谷地田脸上仍挂着笑容。 基督教背景的社会主义者身上往往都有一种宗教倾向,不管他们自认为多么世俗化。我在谷地田身上没有察觉到这点。他身上没有一点宗教热忱的元素——野添亦是如此。谷地田为何会如此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huashengduna.com/hsddx/19751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美国华盛顿发现一艘鬼船,拉到岸上后大家都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