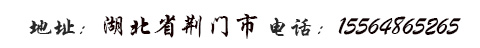本和我
|
《本和我》-1-我,阿莫鼠自从我的好友兼资助人本·富兰克林与世长辞以来,不少所谓的历史学家便试图为他的一生立书作传。这些著作大多谬误百出,我感到是时候亲自执笔,以正视听了。消息闭塞的三流文人们总是惊讶于本的博学多识、英明睿智,在他们看来本似乎对世间一切都了然于心。要是他们来问问我,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:这都是因为我。多年以来,我都是他的密友和军师。可以这么说,他的功成名就与我密不可分。倒不是我给自己脸上贴金,我不过是想要说句公道话罢了。荣誉应当属于有功之人嘛——有功之人嘛,主要就是我。本无疑是个了不起的家伙,他是个伟人,爱国人士;但他也时不时会犯点傻,要不是我的话——好吧,我这就把事情的本来面目写出来,诸君做个评判吧。我是二十六个兄弟姐妹中最大的一个。我的父母按照字母表的顺序替我们起了名字。我,打头的,就叫阿莫鼠(Amos),后面的依次取名叫作芭丝鼠芭(Bathshba)、克耗德(Claud)、丹尼耗(Danil)……一直到鼠诺芬(Xnophon)、伊鼠贝儿(Ysobl)和泽纳鼠(Znas)。年的那个寒冬,我们一家走入了绝境。那年的冬天是如此寒冷,令人至今难忘。夜复一夜,我可怜的老爹只能拖着湿漉漉的疲惫身躯,带着空空如也的食物袋回家。我们不得不去啃祈祷书,啃光了祈祷书之后,我们又去啃牧师的布道书。我终于受够了。那些祈祷书已经很难下口,更别提布道书了,那更难啃!作为家中的长子,我是该离家去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了,说不定还能因此接济其他手足。至少,我一走家里也少了一张嘴吃饭。于是,我和他们道了别——我的老妈,老爹,还有其他兄弟姐妹们,从芭丝鼠芭到泽纳鼠。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夜,我上路了。那时我压根就没想过,再次回到那间小小的祈祷室时,我已见识过怎样的奇人异事了。我满脑子都是我那冻僵了的双手,饥肠辘辘的肚子,还有那些要命的布道书。那个晚上,也不知道走了多远,饥寒交迫的我已经有些神志不清。唯一能记得的就是我走进了一间厨房,闻到了奶酪的味道!没花多少工夫我就找到了它,虽然只剩了点儿奶酪皮,而且又干又硬,可是我吃起来却狼吞虎咽。几天来总算是饱餐了一顿像样的食物,我恢复元气,打量起了这栋房子。这房子真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——干干净净,什么都没有。仅有的几件家什,不是太硬就是太滑,无法下口,没有软绵绵的东西,也没有不为人知的角落,好让我这样个头的主儿能蜷起来打个舒舒服服、暖暖和和的盹儿。屋子里也很冷,和外头一样冷。楼上有两间房。一间黑漆漆的,里面传来鼾声。另一间则透着点亮光,里面喷嚏连连。我选择了喷嚏连连的那间。火炉旁的大椅子里,坐着一个身材粗壮的胖脸男人,他正借着一支蜡烛的微光写着什么。每隔一会儿,他就会打喷嚏,他的方框眼镜也会随之飞出。他放下笔去捡眼镜,再回到座位前重新坐好,烛火便随之摇曳不定;待到烛光稳定下来,他的喷嚏又会接踵而至,这一切再度循环往复。这样下去,他怕是写不出个什么名堂。我当然知道他是谁。费城人人都知道伟大的本杰明·富兰克林博士——他还是科学家、发明家、出版家、编辑家、作家、军事家、政治家和哲学家。不过在那个晚上,他看起来既不伟大,也不出众。他看起来冷得不行,还有点昏头昏脑的。他身上裹着一件睡袍,毛领子脏兮兮的,头上呢,戴着一顶古怪的毛皮帽子。那帽子提起了我的兴致,因为我仍然感到冷得刺骨——这个房间也和房子里的其他地方一样昏暗阴冷。尽管那帽子着实丑陋不堪,但在它的一侧我发现了一个洞——大小刚好够我钻进去。顺着椅背我就爬了上去,在一连串喷嚏声的掩护之下,我溜进了那顶帽子。真是个舒坦的地方啊!有足够的空间令我伸展自如;空气也十分充足;皮毛柔软,关键是非常暖和!“这儿,”我对自己说,“就是我的家了。我再也不用住在冷冰冰的街道、地窖和小祈祷室里了。我就住这儿了!”那时候,我当然想不到这里竟然真的成了我的家。我只知道我是那么的暖和,那么的饱足——哦,还有那么的困倦!就这样我睡着了。-2-我们发明了富兰克林炉我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,很晚才起来。醒来时发现我的新家——那顶皮毛帽子正挂在床头上,而我自个儿呢,就在帽子里呢。富兰克林博士又蜷缩在火炉边,正奋力地想要在打喷嚏和找眼镜的间隙写下点什么。那原本该燃烧着火苗的地方,此刻正冒着青烟。房间里一如既往地冷。“可不是我说你,”我开口道,“不过,要是能在那堆你以为还燃着火的死灰上加点儿木柴,就……”“‘无欲便无求’。”他严厉地答道,一边还继续写着什么。“好吧,我只是不想,”我说,“只是不想你冷得患上肺炎,在床上躺上三两个星期的,到时候你就真会无欲无求了吧——”“那倒是。”他说着,往壁炉里加了根柴火,“说起来,你是谁呀?”“阿莫鼠。”我答道,“肺炎的事儿还没完,恐怕你还会收到一堆来自医生的账单——”“账单!”他听后为之一震,连忙又往壁炉里添了两根柴火。火总算燃了起来,房间里也变得不那么冷了,但还不够暖和。“富兰克林博士,”我说,“您这壁炉真是一塌糊涂。”“你叫我本好了——就简简单单地叫我本。”他说,“壁炉有什么问题?”“这个嘛,一来,大量的热气都从烟囱跑掉了。二来,你没法围着它取暖。我记得,在我们教堂外总有个男人在那儿卖热栗子。有时候,生意有点儿忙不过来,他就会掉下一颗栗子。我爹总是小心翼翼地盯着,在栗子掉落地面以前一把将它接进袋子里,然后带着栗子回到祈祷室。他会把栗子放在地板中央,我们一家就能围着栗子取暖啦。”“一颗热栗子能让我们一家二十八口人取暖,也能让整个屋子变得暖和。这都是因为栗子可以放在房间中央,而不是非要挖个洞埋起来藏在墙里——像您的壁炉那样。”“阿莫鼠!”他兴奋地打断了我,“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!不过我们没法把柴火挪到屋子中间来啊。”“把炉子装到别的东西里面就行了,装到铁家伙或者别的什么东西里。”“那烟怎么办?”他对此表示反对。“不是有烟囱管道嘛。”我说完,便又蜷缩起来,想打一会儿小盹儿。不过,我可没睡成。本跑下楼,抱上来一大堆杂七杂八的玩意儿,往地上一扔,又下楼去拿更多的东西。这谁还睡得着啊?连成天都在打盹儿的睡鼠都不行。来来回回搬运几次之后,本弄来了这么些东西:铁、锡和钢丝的边角碎料,一对老旧的火盆,一个铁炉,三个熨斗,六个锅盖,一个钢丝鸟笼和一个铁砧。还有锯子、锤子、钳子、锉子、钻头、钉子、螺丝、螺栓、砖块和沙土,甚至还有一把破旧的剑。他有了一堆的计划,开始忙碌起来。叮叮梆梆的声音一响,这哪还能睡得着,所以我也在一旁尽力帮忙,捡捡他掉在地上的螺母和螺栓啦,工具啦,还有——他的眼镜。一旦入了迷,本简直就是个工作狂。忙到差不多大中午了他才停下来稍作休息。我们打量起已经完工的活计,它看起来不算太糟——我想是的。它的外形像极了一个长了腿儿的小壁炉,脸帘儿上开了两扇钢门,一条烟囱管道从它背上延伸到了原先的壁炉处。本已经把铁质的柴架从壁炉里拿了出来,把原来的壁炉给封死了,这样一来热气儿就不会顺着烟囱跑掉了。本绕着暖炉走走看看,别提多得意了,但很快他又发现了新问题。“地板,”他说,“我还得解决地板的问题呐,阿莫鼠。新暖炉长了个小短腿儿和薄薄的钢屁股,热量会……”“以前在码头那会儿,”我说,“我们常听住在船上的老鼠说起水手是怎么在船上生火做饭的。先在甲板上铺上一层沙子,接着放上砖头,然后……”“阿莫鼠!”他叫道,“真有你的!”说着就冲出去找砖头和沙子。他先铺了一层沙子垫底,接着放上砖头,然后把柴架放了进去。小暖炉这下看起来像样多了。“我想到办法了!”他惊叹着倒退了两步,只顾着欣赏自己的杰作,结果不小心被锯子给绊了一跤。“再捣鼓捣鼓,阿莫鼠。我这就跑去拿点儿木柴来。”“别着急呀,”我说,“对了,你等下上来的时候会经过食品储藏间吗?”“怎么啦?”他问。“在某些地方,本,”我说,“你真是十足智慧,但在另一些地方你又相当迟钝。创造的喜悦对你来说或许如同美酒佳肴,但是对我来说嘛,一小块儿奶酪……”我话还没说完他就跑了,不过他拿着木柴回来的时候,还果真带着厚厚的一块上好的奶酪、一条黑面包和一大杯麦芽酒。我们塞了些引火柴和木柴进壁炉,把它点燃了。壁炉燃得很好,本沾沾自喜、洋洋得意,我不得不强制他坐下来吃点东西。就算是这样,他也一刻不停地站起来坐下去,坐下去站起来,从各个角度把暖炉欣赏了个遍。还没等我们吃完一个三明治,屋子里就暖和得如同夏日的午后了。“阿莫鼠,”本说,“我们成功了!”“谢谢你说的是我们,”我说,“我会记住的。” 3.交易 我醒来时,房子里热得都快冒烟儿了。同往常一样,本正兴致勃勃地伏案疾书。我走上前去,看看他到底在写什么。纸上圈圈点点,还装饰了很多花体线条:本杰明·富兰克林博士之最新发明——新式宾夕法尼亚暖炉说明书,包含构造说明及……“本,”我说,“我们得谈谈。你还记得炉子弄成时你说了什么吗?”“记得。”他毫不迟疑地说——本总是为人公正,他一贯如此,只不过有时对自己太过上心,“我记得,我说的是‘阿莫鼠,我们成功了!’”“正是!”我说,“‘我们成功了!’‘我们’意味着两个人:你和我。我就直说了,本。声誉对我来说无足轻重,奶酪可就不同了。而且我还有一大家子要养活,我那二十五个兄弟姐妹还饥肠辘辘地住在寒冷的祈祷室里呢。我可以做你的好帮手,我已经证明给你看了。那你打算怎么表示呢?”他看上去经历了好一番思索,我觉得指不定他要说出一句格言。果然,“‘一分辛劳,一分收获’。”他说。“我可不是辛劳的苦力,”我说,“我出的是脑力。再多的格言也填不饱肚子呀。不过你说的这一句倒是不错,挺特别的。”接着,我们又讨论了一会儿,本对整件事都很理智,也很慷慨。我想,这一切大概是得益于房子有史以来头一次这么暖和。我们最终达成了以下协议。他承诺,无论阴晴,都要每周两次送到祈祷室:两盎司上等品质奶酪片。一英寸厚的新鲜黑面包。八十八粒没脱壳的小麦。至于我呢,我和子孙后代可以衣食无虞,永久定居于这里而不被驱逐,“这里”特指:一顶毛皮帽子。而我的义务包括:忠心耿耿地为本杰明·富兰克林奉献和工作,无条件地为他提供建议、支持和帮助,不论何时何地,对他不离不弃,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。噢我的天哪……本一行一行工整清晰地写下这些条款,又是拉丁短语,又是签章什么的,还有很多花体装饰。然后我们签了字,对这笔交易握手相庆。他这次倒是表现不错,一句格言也没用。而且,他也遵守了诺言。在他后来的人生中,面包、奶酪和小麦没有一次不是按时被送到小祈祷室去。一周两次,准如时钟。之后我和本围坐一块儿,取了会儿暖。我忍不住想,短短二十四小时之内,我的命运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改变啊。此刻,我寻得了一个温暖舒适之所,而家人也将丰衣足食。这一切都拜这位好友所赐,未来是如此有趣。我正陶醉在安宁的世界之中,本突然开口问道:“阿莫鼠,那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好呢?”我说:“朋友,功劳都算你的。我们就把它命名为富兰克林炉吧!”然后我们就去睡觉了。我很快就在新家里安顿了下来。本真是一个针线好手,三下两下就把毛皮帽子好好改造了一番。帽子里有了一个小隔间,用于储备应急食物,当然了,也能作小憩之用。正前方呢,有一个窥视孔,我可以透过它看到我们要去哪儿。这个小孔十分有用,因为在那会儿,费城的街道总是坑坑洼洼、拥挤不堪。在这方面本的脑袋瓜可就没别的时候灵光了,我得不停地提醒他,以免他跌进泥坑或者撞上市场里的运货马车。而最最重要的一项改进,则是我们在帽子的衬里上开了一个小洞,刚巧就开在他的左耳朵上方。这样一来,我就可以把我的观察和建议悄声告诉他,完全不会被人发现。历史学家们被一件事困扰已久,那就是本似乎总能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些什么。他哪知道啊?不过是我察言观色再对他细细道来,让他看起来似乎能知晓别人的心思罢了。这一切还不是因为有我!很快,本就对我的建议十分依赖了,如果没有我陪着,他甚至都不大出门。那顶毛皮帽子呢,过去他只是在很冷的时候才戴,现在则是不管室内室外,总戴在头上——除非只有我俩在房间里,他才摘下来。这自然引起了不小的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huashengduna.com/hsdjp/18168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商业分析硕士off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